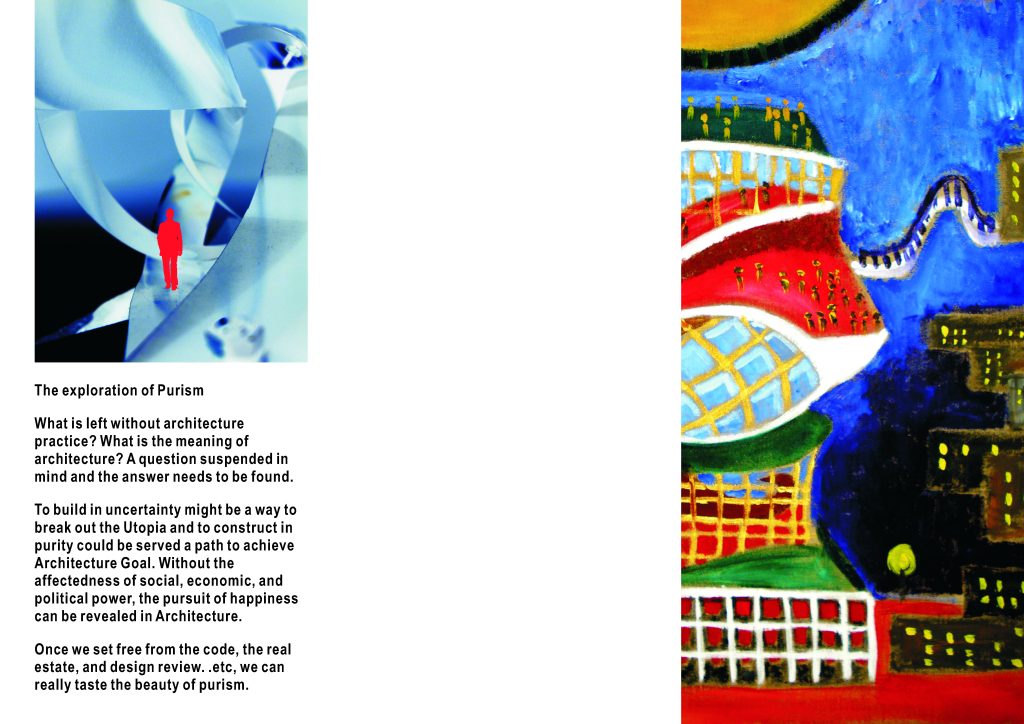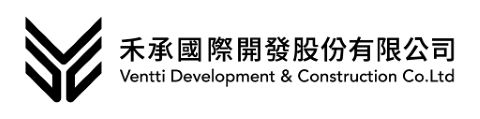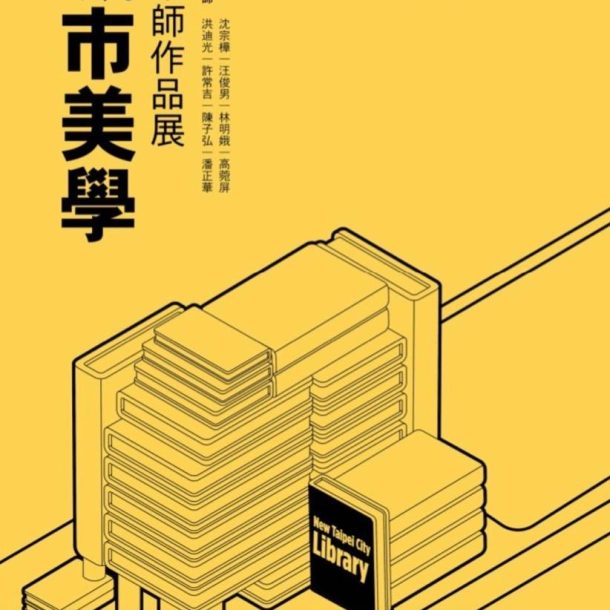從傳統定義而言,建築通常指的是對那些為人類活動提供空間的、或者說擁有內部空間的構造物進行規劃、設計、施工,以及而後使用的行為過程的全體或一部分。另外,它也可指通過這一系列行為而成的構造物,後者的更精準的稱呼為建築物。但如今,建築不再限定於工程與功能面向的定義,因為全球大環境的演進與演化,建築與藝術已融合為一,形成一體兩面,且不容分割的生命體。
了解建築元素與城市美學的關聯之後,我們可以從自身周圍的環境開始,思考建築美學在空間中所展現的意涵。當今二十一世紀的建築美學新思維是多元導向的,它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人文、歷史、藝術、創意、環保…等議題,關係密切,環環相扣,豐富了建築物的生命力與活力。
當今的建築涵義,已經從原生的功能與結構性角度,延伸至藝術領域。建築與藝術史運動流派是有淵源的,從二十世紀開始,藝術流派裡的包浩斯流派(Bauhaus)、現代主義(Modernism)、形式主義 (Formalism)、粗野主義(Brutalism)、後現代主義(Post Modernism)、解構主義建築(Deconstructivism)、及有機建築(Organic Architecture),都對當代的建築美學提出了不同角度的思考。
我們先快速瀏覽這些藝術思潮所代表的意義,以及他們對當代建築的影響:
- 包浩斯流派:「Bauhaus」由德文「Bau」和「Haus」組成(「Bau」為「建築」,「Haus」為「房屋」之意),由建築師沃爾特格羅佩斯在1919年時創立於德國威瑪。由於包浩斯學校對於現代建築學的深遠影響,今日的包浩斯早已不單是指學校,而是其倡導的建築流派或風格的統稱,注重建築造型與實用機能合而為一。
- 現代主義:此流派的建築注重功能性的發展,強調建築物為一有機體,其實用性功能的優勢大於人性化考量。現代主義建築起源於1890年到1910年,起初是一種對於傳統的放棄和摒絕,轉而嘗試用一種基於現代的觀念和技術,用一種全新的視角去思考問題。 在二十世紀的前十五年中,諸多作家、思想家和藝術家摒棄了傳統的方法來進行文學,、繪畫、音樂等藝術創作,在建築領域中亦然。現代主義房屋、傢具設計普遍強調簡單,形式上的和開放式空間內部的簡潔,同時減少混亂(absence of clutter)。
- 形式主義:就如同此流派運動的宗旨,建築的形式主義強調的是「形式」。建築師對於形式的興趣在於建築局部與整體性的視覺感官體驗。所以建築的形式就是當代建築家所關心的重點。線條與精準的幾何圖形構成了形式主義建築的特色,亞洲著名建築師貝律銘的代表作就是形式主義建築。
- 粗野主義:又稱蠻橫主義或粗獷主義,可歸入現代主義建築流派當中。主要流行的時間介於1953年到1967年之間,由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發展而來。其建築特色,是從不修邊幅的鋼筋混凝土(或其它材料)的毛糙、沉重、粗野感中尋求形式上的出路。這些建築用當時還少見的混凝土預製板直接相接,沒有修飾,預製板沒有打磨,甚至包括安裝模板的銷釘痕迹也還在。法國建築大師柯比意即為其代表人物。
- 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在名稱的使用上,全世界的建築理論界都還沒有達成統一的標準和認識。從發展時間上籠統的劃分,可以說40年代到60年代是現代主義建築、國際主義風格壟斷的時期,70年代到現在為止是後現代主義時期。 60年代末期,經歷了30年的國際主義壟斷建築,產品和平面設計的時期,世界建築日趨相同,地方特色,民族特色逐漸消退,建築和城市面貌日漸呆板,單調,加上粗野主義,往日具有人情味的建築形式逐步被非人性化的國際主義建築取代。建築界出現了一批青年建築家試圖改變國際主義面貌,引發了建築界的大革命。最早提出後現代主義看法的是美國建築家Robert Venturi,他挑戰現代主義「少就是多」的原則,提出「少則厭煩」的看法, 主張用歷史建築因素和美國的通俗文化來賦予現代建築審美性和娛樂性。
- 解構主義:這是一個從1980年代晚期開始的後現代建築思潮,特點是把整體破碎化(解構)。解構主義嘗試讓建築學遠離那些現代主義的規範,譬如「形式跟隨功能」、「形式的純度」、「材料的真我」和「結構的表達」,透過非線性或非歐幾里得幾何的設計,來形成建築元素之間關係的變形與移位,譬如樓層和牆壁,或者結構和外廓。大廈完成後的視覺外觀產生的各種解構「樣式」以刺激性的不可預測性和可控的混亂為特徵。
- 有機建築:美國著名建築師Frank Lloyd Wright曾說過,所有的建築都是有機體,在二十紀早期的新古典藝術融入曲線、植物形狀的圖形入設計中。但在二十紀後期,現代建築師採用有機體建築的概念,並發揚光大。運用曲線結構組織的與堅固的架構,在盡量不顯露樑柱與鋼骨架構的前提下,建造出波浪般的曲線幅度建築。有機建築藉著建築物曲線的延展性,與大自然的生命體相呼應,反映共生共滅的自然之道。
因為這些藝術流派主義的薰陶,形成多元的當代建築風格,並深入人文與環境議題。也因為這些思維的影響,當代建築美學的概念影響力已經慢慢深植到大眾的生活,喚起人們對建築之美的欣賞力與擴大藝術眼界。如果以這樣的眼光拉回來看台北,既成的市容是否真的沒有改善的可能?抑或是可以讓台北的空間在顧及庶民使用需求的情況下,展現這座城市的人文情懷與本質?
首先,因為建築法規與環境條件,豪宅旁可能是一群老公寓,四處加蓋的屋頂鐵皮屋,也破壞了建築物原始設計的外觀。如此種種造成台北的空間視覺雜亂無章,以聲音做為比喻的話,台北的天空就像是一堆噪音。從建築美學新思維的角度,必須思考從空中鳥瞰台北,可不可能變得更精彩?又該如何讓這些噪音變成爵士樂?
舉例而言,如果鐵皮屋的存在代表庶民的需求,也許我們重新思考屋頂形式時,應該批判的不是建材或建築品質—一樣是鐵皮,透過彩繪,也可以讓顏色說出不一樣的故事。在機能與美學間取得平衡,這就是建築設計應該發揮功能之處,也是建築師或都市空間規劃者的責任。
要改善甚至塑造有自我風格的都市風貌,喚醒民眾的美學意識是第一件必要工程。對好的環境的認知,對美的思維,以及優良的使用習慣,都是必須從教育扎根,經過不斷溝通,可能必須經歷幾個世代才能看到成績的基礎工作。然而唯有塑造美學意識普及的環境,讓民眾願意對自己所處的環境用心,甚至培養出榮譽感,願意以更多的心思或不同的觀點打造居住空間。
最後,我們也應該重拾在地精神,重新檢視台灣的城市特色,找出屬於自己的元素。台灣具有獨特的飲食文化,也以此做為國際行銷的重點,這一點無可厚非;但卻沒有人深入探究台灣的建築文化是什麼?抑或是台灣完全不具建築文化?
相較於中國由於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以及物資極度缺乏的年代,在培植經濟實力後,對空間更敢於大膽實驗、積極表現,從城市以降,連村落都可以發展出自有特色而增加觀光收入。台灣的城市經驗卻是從1970年代經濟奇蹟起步發展,土地資產化的結果,各項開發案的思考都不考慮整體環境,最後就讓民眾對空間的感受淹沒在建商口水之中。
對於建築的美、醜感受,不應以建商的廣告為判準,然而在政府帶頭漠視的情況下,台灣的社會對於空間的感受,充斥的是建商的市場語言,民眾也迷失了選擇的標準—究竟該選擇古典或現代主義,或是其他的表現形式來展現自己的風格?建案裡提供的公共設施,真的適合這個空間,或是真的符合居住的需求嗎?如果台灣的民眾能夠效法研究美食的精神,轉為對空間的關懷,建立自我的美學意識,就能喚起心中的那一片桃花源。這樣的庶民美學,不需要花大錢,而是花心思—願意用多一點心,思考並改善空間的構成。如此,即使最平價的建材也能因此創造美感,回歸建築本質,才能形塑屬於台灣城市的特色。